




2019.11.25(下午&速记稿))面向未来的美术教育.docx
40墨值下载
面向未来的美术教育
2019.11.25
凌敏:各位院长、各位老师、各位参加开幕式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这里也是我
们开篇讲座请了全球十位院长来讲。先说一下
FutureLab
,创意未来艺术与教育博览会,
全世界一年有很多的博览会,但是这个博览会比较特殊,特殊在哪里?是因为教育,是因
为美术和设计教育,是因为畅想未来的美术与教育吗?是。首先代表
FutureLab
的组委会
代表周天海(音)总监,对大家各位的到来表示欢迎。
为什么要做一个以教育、以艺术和设计为主题的博览会?因为我们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
新时代,其实带来的新技术、新功能、新方法、新愿景,也带来了全融合的时代。所谓融
合就是跨越,跨专业、跨技术、跨地区、跨国界、跨文化,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里,我们
的教育会怎么样呢?
所以今天我们请了十位著名院校的院长来谈教育问题,但是我们的问题又非常简单,似
乎不是一个学术的问题,我们就说美术和设计学院最应该学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简
单又很难的问题。
我们的顺序是这样的,今天由十个院长来谈这个问题,谈完以后有一分钟的时间回答一
个简单的问题,每位院长有
15
分钟时间。我们先请第一位演讲的,是中国美院副院长高
世明教授,大家欢迎!
高世明: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在艺术学院里应该学些什么?在今天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巨
大的变局当中。
150
年前尼采放言要重估一切价值,今天我们似乎又在面对同样的历史关
口。这些年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都有一种感觉,技术正在加速,世界正在加速,我们正在切
身参与一次极具颠覆性的技术和认知的变革。同时我们也共同在见证一个哲学、艺术、技
术、政治和伦理都在全面重构的时代。
对艺术教育而言,教与学,艺术的感性经验,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甚至人的形态和我的
意义,都正在这场技术的加速度中被重新定义。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想象一种艺术教
育的新方式和新框架?对新方式和新框架的想象,未必是一味地瞻望未来,未必一直往前
走,有时候也意味着要回溯本源。中文非常古老的“艺”字,原初的写法本来是一种种植和
培育,这在我们艺术与教育那种原始的关联性,二者都统一于人的成长与培育。
同样在古希腊人的经验中,哲学教育和艺术都是作为一种自我的技术,统一于古老的神
谕,关心你自己。根据福柯的考察,这个神谕本著名的德尔斐神谕也就是认识你自己更加
根本、更加古老。这里所说的关心,既是指一种侍奉,同时又是指训练,同时也意味着沉
思,指向福柯所谓的精神性,也就是主体为了达成真理用来塑造自己的探究、实践与体验。
在二十一世纪最初二十年,技术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巨大落实,人的发展更加瞠
乎其后。今天我们必须重新发明一种人学,这需要我们重新回归到艺术和教育的本源,就
是关心自己,并且重启一种自我的技术。当下艺术和教育的根本责任,就是在大数据、人
工智能时代推进人的保存与人的发展。为此学院和教育者们需要构建一个多元化的思想空
间,需要重新思考艺术和教育、创造与传播、生产与消费、社会与自我之间的复杂关系,
我们需要共同追问面对技术、信息、资本全力网络构建起的总体性的全球治理,我们如何
重塑艺术的创造和艺术的教育。面对这种全球治理所带来的新的生命政治,作为一种仁学
的艺术和教育应该如何展开。
最近
40
年以来,各种新技术构建起了人类各种各样的“假肢”,这种庞大的假肢体系正在
废除我们的感官、废除我们的感受力,割裂我们的身心。未来人类的根本困境就是感性贫
困,身心分离。
在此艺术或许有所作为,他必须要有所作为。这两年我一直反复提醒我们有两个
AI
,一
个是人工智能,另外一个是艺术的智性,而艺术智性通达的就是一种上手的记忆开启的知
识,一种感同身受的知识,一种身心发动的知识。
在我所在的中国美术学院有三种不同的教育观在同时起作用,第一种教育观认为学院提
供的只是土壤,园丁的工作就是培育土壤,让土壤尽可能养料丰富、成分多元。学院的任
务是把这片土地养好,让学生在最好的土壤中自由生长,这种教育观我们称之为“土壤论”。
第二种教育观是“锻炼说”,认为艺术教育就像锻钢打铁一样,在敲打中把铁中的杂质逐
渐剔除。越敲打钢铁越精髓,这种教育如同匠人的修行,是学而后习反复琢磨,是在劳作
中养成精神的体验。在此这种艺术教育的过程,也就是自我创作的过程。
第三种教育观是“感染说”艺术中最根本的东西是无法教的,只能唤起。每个人的身上都
有创造的种子,艺术的任务是唤醒他,使他苏醒发芽。这种意义上的教育像是某种心情的
传递,甚至像是医学上的感染。通过这种感染,一个人开始变得善感、开始变得不满、开
始变得更加敏锐、开始变得渐渐渴望改变。
of 33
40墨值下载
【版权声明】本文为墨天轮用户原创内容,转载时必须标注文档的来源(墨天轮),文档链接,文档作者等基本信息,否则作者和墨天轮有权追究责任。如果您发现墨天轮中有涉嫌抄袭或者侵权的内容,欢迎发送邮件至:contact@modb.pro进行举报,并提供相关证据,一经查实,墨天轮将立刻删除相关内容。
下载排行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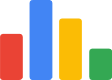

评论